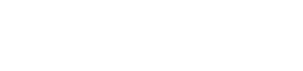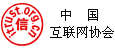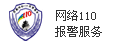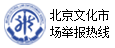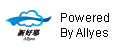愤怒的女性终于不再是“麻烦” 但这依然不够

BBC2017年版《小妇人》里的马奇太太 图片来源:Patrick Redmond/BBC/Playground
我(本文作者Emilie Pine,都柏林大学学院副教授,作家)很清楚抛开脚本的女性会面临的后果。今年早些时候我出版了一本收录六篇私人文章的书,全是关于那些女性本不该说出口的事情。我很担心公众的回应,害怕被人打上惹是生非的标签。我确实惹是生非了——不过大体来说是正面的。每天我都收到读者的电邮,感谢我谈论酗酒、不孕和性暴力的话题。
收到的少许负面反馈之一来自于一个电台记者,他问我是如何——而不是为什么——选择去描写15岁被强奸的事情。他问我,为什么我没有把强奸描写放在书的开头去“抓住读者的眼球”?他的问题让我很惊讶,而采访结束后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又为什么要在电台直播里问我?他的问题好像是说,我描写遭强奸唯一可能的理由是把它用作武器。我体验过的一切情绪——狂怒、悲伤、悔恨和恐惧——被缩减为一种:愤怒。看起来似乎有了一种新的脚本:愤怒的女人这种脚本。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喜欢这种脚本。
我11岁的时候读了露易莎·梅·奥尔科的《小妇人》。和所有想当作家的女孩一样,我将乔视为偶像。最近重读这本书,我再次体会到了之前所爱的很多东西,比如乔的强韧性格,比如她靠写作独立生活的能力。但是当我读到母亲马奇太太的这段话时我惊住了:“我生命里几乎每一天都很愤怒,乔,但我必须学会隐藏……我学会了克制已经到嘴边的话。当我感觉靠意志无法阻止这些话脱口而出时,我就走开一分钟,为自己如此的软弱和邪恶而发抖。”马奇太太给乔的建议是:压制你的愤怒,因为原因不在于问题——原因在你自己身上。
当那个采访者要我解释描写强奸的方式时,我并不愤怒。我是那么地渴望被人喜欢,所以我只说了那是“我的人生和我的故事”,没有再多说。我是否因为小时候将马奇太太的建议内化在心所以克制了自己?我应该做出愤怒的反应吗?
而今,当此前一直被视为问题的女性愤怒被看作一种解决办法,是否每个女性每时每刻都有义务表现出一点愤怒?现下时刻似乎需要我们个人的和集体的愤怒——如Rebecca Traister所言,“愤怒的窗口现在已经打开。”然而这种愤怒非常复杂。我发现自己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反思它突然达到的规模,想知道这个窗口还能打开多久,是否有一种正确类型的愤怒,或是表达愤怒的正确方式。我还想知道,如何能在这个窗口里写作和发声,而不至于把自己从窗口抛出去。
乔为了取悦母亲而平息了自己的脾气,或许我需要一个比顺从的乔更贴近时代的文学楷模。所以我转向书架,看看21世纪的小说里,女性从愤怒里获得了怎样的回报。这些小说里常有发怒的女性——她们强大而激励人心,让人恼怒,以不服从为乐。但这些女性也因为愤怒而遭到惩罚。在克莱尔·梅苏德的《楼上的女人》里,诺拉的第一句话似乎预示着愤怒的爆发(“我有多生气?你不会想知道的”),但实际上只是挑起了她自己的伤痛。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的莉拉,因为她充满激情的自我奋斗而被贫困、暴力和失去孩子反复惩罚——似乎愤怒的历程只带来了负面的后果。
这是一个我努力想要平复的悖论——因为做了或说了我们不敢的事情而被我们喜爱的那些虚构角色,也承受了最严厉的惩罚。愤怒的形式或有不同——从内奥米·阿尔德曼的《力量》一书里的全球女权主义者崛起到伊丽莎白·斯特劳特《微不足道的生活》里静默的、私人的愤怒——然而惩罚都是一样的。尽管她们都是读起来惊心动魄的角色,但她们的话语和行为所收获的结果,最好的也不过是疏离和孤独,而最坏的结果,是强奸和死亡。即便将故事为社交媒体的一代人重新创作——如卡米拉·夏姆斯在《家园之火》里对安提戈涅神话的改编——女主角最后仍逃不过一死。我想知道为什么女性角色似乎仍然命定要说出那些将她们推向惩罚和死亡的台词。我们真的没有走出安提戈涅,或者海达·高布乐,或者《觉醒》吗?

《失踪的孩子》
[意]埃莱娜·费兰特 著 陈英 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7
女性愤怒的颠覆性力量并未带来乌托邦式结局,我对这一点感到失望,并非因为我给女性作家设定了不合理或者达不到的标准。我的沮丧是因为她们给出的诊断是如此的尖锐和准确。因为女性不只是在书本里因愤怒而遭受惩罚——这些小说是我们每日在生活中和网络里看到的攻击和羞辱的镜像。社会应该早于小说情节发生改变吗?小说是引导改变,还是仅仅只是改变的事后反映?
愤怒好像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恒久的生存状态了。聆听女性的愤怒这一文化转向,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有时候人们感觉大声地表达愤怒已经成了一种要求,而不是一个选项。从前女性的情感活动集中在压制愤怒上,现在我们则将自己的痛苦展现给公众的凝视,而他们常常并不感到同情。想想这些标签的名字吧:#我也是,#是时候了,#为什么我没逃走,或者#为什么我没有报警。对女性的要求很多——她们不仅要识别并努力纠正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还要吞下抗议的情感和社交后果。抗议是必需的,但它也让人筋疲力竭。
当我在看《汉纳·盖茨比告别秀:娜娜》时,我满脑子都是这些问题。这场演出号召愤怒的女人们行动起来。盖茨比揭露了恐同的文化氛围迫使女同性恋者进入的那种自我贬损的脚本所带来的伤害。她要求叙事方式的改变——既包括她的,也包括我们的——以适应她的愤怒。然而,在这场秀的最后,盖茨比说她已经对愤怒感到疲惫了。她说,愤怒本来是一种团结人们的方式,却最终只是在散播“盲目的仇恨”。这是一种双重的束缚。我们需要愤怒来揭发不平等和暴力,我们需要愤怒去激起回应,我们需要愤怒驱动我们做出改变。但愤怒会给我们留下伤疤,会消耗我们。这是一个有益的警告。
盖茨比请求我们讲出自己的故事但抵制愤怒,这与马奇太太对乔的建议绝不可同日而语。就像人们不再默认地认为女性应该动摇自己,现在,我们被要求去摇动这个世界。但是允许女性表达愤怒并不意味着19世纪对女性和权力的态度已经从我们身上移除了。当人们因为我写出了那些不该说出口的事情而称赞我“勇敢”时,我想说:“我并不是勇敢——我是很愤怒。”然而,通常我什么也不说——因为我知道会有被人贴上愤怒标签的危险。还因为,和盖茨比一样,也许也有点像马奇太太,我不信任愤怒的能量。如今,当女性表达强烈的观点或者坦承痛苦的经历时,也只被视为愤怒,而不是其它的情感能力或智识能力,我对这种方式也不信任。
因此,虽然我享受阅读书本里的愤怒女性人物,也感恩那些发起反对不平等和暴力的运动的愤怒女性,我最期望的还是另外一些事情。我希望现在能关注比愤怒更多的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永恒的空间,在其中女性可以同时有多个面向。我们有这么多故事要讲述。让我们完全抛开脚本吧!
首页推荐
热门推荐
图集
点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