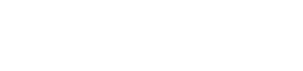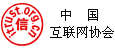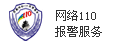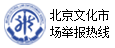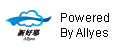莫言:我们这代作家写的农民,应该比鲁迅写的更丰富

活动现场
凤凰文化讯(冯婧报道)2012年12月10日,荣获诺奖的莫言与陈思和、曹元勇一道,参加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的颁奖仪式。在大雪纷飞的北欧,滞留机场的莫言想,如果能把这大雪挪到常年干旱的家乡高密多好啊。颁奖当天,诺奖委员会秘书的女儿刚刚出生,这让他想起归葬于大地、在迁移中最终荡然无存的母亲的尸骨。如果说,十个小时的飞行距离让莫言感受到了世界对于渺小个人的无限广袤,生命的轮回则彰显了个体内部的断崖与纵深。
五年之后,斯德哥尔摩加冕之旅的原班人马齐聚思南公馆,与读者们一同分享“中国文学传统的当代继承与转化”。本场活动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主办,曹元勇主持。莫言领诺奖前的所有虚构作品,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版权全部推出,包括11部长篇小说,七部中段篇小说,两部剧作集。

莫言作品全编
莫言:文学传统中重要的是民间的、口头的部分
曹元勇介绍道,任何一个时代作家写作,都面临着如何继承自己民族文学传统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还不可避免地受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譬如,莫言老师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往往让人想到马尔克斯或者福克纳。莫言对此并不讳言,正是这些文学大师启迪了他,让他知道作品可以这样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要远离他们的影响。莫言作品中的另外一个源流则是传统文学,从《檀香刑》、《生死疲劳》、剧作《荆轲》等作品中都能感受到这种紧密的血脉关系。
莫言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包含两个面向,这两种传统都是汉语重要的构成部分,也是从事文学创作宝贵的资源:一方面是经典化的文学遗产,包括先秦的散文、诗经、史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形式在内的文学史脉络。读者可以在莫言的作品中一一找到这种对照:如长篇小说,例如《檀香刑》,就是一部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又如《生死疲劳》的叙事结构则借用了中国佛教传统中六道轮回的形式,包括中短篇小说创造性地利用了《西游记》《聊斋》等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地狱、幻境等神秘意象,使作品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包裹在丰富的叙事艺术中而表达出来。而莫言的话剧剧本《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则是用现代思想对众所周知的经典历史传奇故事的再创造。
另一方面则是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包括民间说书、戏曲、俗言俚语甚至生产队的饲养棚里讲述的故事。对于莫言个人而言,民间文学对自己的影响比书面经典要大。他小说和剧作中所呈现的民间传说、故乡风情、奇闻异事、乡土小调,既是他童年时代记忆和幻想的产物,也是中国民间传统和民间文学主题的拓展和现代升华。“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要从经典作品里面继承文学传承的话,很可能我们所利用的资源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民间文学这个传统好好利用,就会形成丰富性和多样性。人类世界艺术最重要的特征和最宝贵的素质就是丰富性和多样性,民间文学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多样性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学传统重要的是民间口头的,在一代代流传的。”

陈思和
陈思和:真正作家一定是从现实生活的矛盾中产生
陈思和进一步引申道,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中所谓的传统都有两种:一种是跟今天没有关系的、已经死掉的传统;还有一种则是和今天还有关系的、活的传统。这种活的传统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文学而言,一个作家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他的现实生活,要在生活当中认识和寻找民族文化力量的源泉。“大家千万别以为背了3000首诗就能成诗人了,把四书五经都读通了就会变成作家,真正作家一定是从现实生活的矛盾中产生,现实生活中深层次的地方就有中国文化的传统。”
在陈思和看来,莫言小说创作的过程,是对民间文化形态从不纯熟到纯熟、不自觉到自觉的开掘、探索和提升,不存在一个从西方魔幻到中国传统的撤退。“中国文化传统喜欢讲鬼故事,讲动物成精”,陈思和以莫言的《生死疲劳》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席方平的故事为例,指出莫言作品中一切魔幻的变异的荒诞的因素,都与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紧密关联。两个故事讲述的不只是沉冤昭雪的过程,而是中国文化中坚韧不拔的、争气不争财的精神,与一切不公正的现象抗争到底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今天还在产生世俗层面上的战斗意义。莫言对中国民间农村有着非常深刻理解的作家,在这个意义上,莫言的创作跟中国民间文化是相通的。
莫言解释道,《生死疲劳》中之所以写这么多动物,一方面源于中国上古神话中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人定胜天的故事,也是因为自己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动物也具有这样的个性。跋涉300多里路回家与小猫团聚的断尾老猫、装病耍赖打死不干活的大黑牛,都被莫言用到了自己的小说里,“当时我们就说这头牛一定前世是反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所以不给人民公社干活。写小说的时候,因为主人公是地主,地主对人民公社怎么满意呢?所以地主转世变成了牛绝对是不给人民公社干活的,当年的那些玩笑后来都用上了。”

莫言
莫言:我们这代作家写的农民,应该比鲁迅写的更丰富
但无论是母猫的故事还是夸父追日的故事,在莫言的笔下都好似发生在当下。陈思和指出,莫言完全是一个民间作家,很多资源从民间来的,但是莫言对于这些素材的处理完全是经过现代人的思维和审美的方式,没有给人感觉到他是一个很土的作家。《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手指被烧红的铁烧焦了却梦到闪着金光的萝卜的小孩,就是莫言创造的一种奥秘,将自己经历的苦难转化成一种艺术上的正能量的东西,变成一种美,这个转化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转化,莫言所有的小说都有这样一种力量在里面。
莫言认为,所谓的民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概念,人们一提到民间往往想到穷乡僻壤、荒山老林和农村渔村,实际上民间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上海难道就没有民间了吗?高楼大厦里面照样有民间。每个作者都应该了解自己的生活圈子,了解自己身边的人,熟悉自己身边的事,要从身边熟悉人的言谈当中发现语言的新元素,充分吸收他人生活当中的艺术情节。充分熟悉老百姓的语言,并且从中提炼出文学语言来。这个民间谁都有,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在农村长大的才有,即便在上海、香港、美国都是有民间可写。”
在现场提问环节,有读者试图比较鲁迅和莫言笔下的乡村以及知识分子。陈思和认为,中国文学有三个部分;一块是官方的;一块是知识分子或者革命者的;还有一块是民间的,老百姓的。鲁迅一出来把农村看得很低,主要刻画闰土、阿Q这样的农民是不可取的,知识分子要启蒙农民,唤醒他们去革命。而莫言写的就是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可是莫言在他们生活当中看到了他们的力量,他们生存的机制和方法。莫言对农民的理解,远远超过五四知识分子对农民的理解。为什么鲁迅小说里面的人物从来没有进到房间里面去?为什么阿Q都是在广场上?因为他们只能看到公众场合的农民,不知道农村在家里面怎么吃饭睡觉,那农民当然是沉默的。而莫言的小说真的能够把农民当一回事,不是代农民讲话、为农民伸冤,是直接把农民所受的苦所经历的委屈那种无奈,那种被损害和被侮辱的感觉端出来了。莫言小说里面的知识分子没有好的,因为中国农民遭受的苦难,在知识分子眼里是微不足道的,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知识分子就特别轻率可笑。
莫言则认为,农民形象的变化与大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并不是前辈作家不如当代,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农民本身发生了变化,也因此,作家的持续创作才有可能。 “鲁迅先生塑造的农民更多是愚昧、麻木、逆来顺受的。而我所描写的农村农民,和30年代已经有了变化,尤其是跟我同时代的农民身上,不仅仅有逆来顺受,也有抗争的一面,除了有哀愁的一面,也有狂欢的一面。我们这代作家作品里面描写的农民,比鲁迅那个时代的作品里的形象更丰富了。至于知识分子看待农民和农民看待自己,他们的立场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这也是我们这代作家和上代作家视角的区别。”

莫言中短篇小说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
莫言:一个小说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剧作家
民间戏曲对莫言的影响非常大。高密号称有四宝:剪纸、泥塑、年画还有冒腔。莫言回忆道,自己小时候没有电视和电影可以看,从小就看乡野广场或者集市土台子上的乡村戏班子演出冒腔,文革期间村里面的小孩跟大人也把样板戏、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改编成冒腔,“大家可以想象那么严肃的样板戏被冒腔一唱会是什么样,我们演不了英雄人物,就演小土匪,刘副官这种小角色,化妆也自己管,每个家有锅灶上面有灰往脸上一摸就上台了”。
莫言对民间戏曲既非常熟悉,也很有感情。对戏剧创作也一直很感兴趣,在山东黄县现在的龙口当兵时,模仿《于无声处》、《雷雨》、《屈原》等知名剧本写了很多部话剧。一直到1999年,转业离开部队,替部队话剧团改编了《霸王别姬》的话剧版,在小剧场里面演了一个月,反响不错。“司马迁在书上写的你不要改,没有写的东西你可以发挥。让吕后爱上了楚霸王,跑到楚霸王的大营里面毛遂自荐,太离谱了是吗?”
《檀香刑》则是小说化的戏曲,或者戏曲化的小说,整个小说完全按照戏剧剧本的构思来写的,人物设置是高度脸谱化的,人物关系也充满戏剧性,语言更是大量使用了冒腔的唱词。《我们的荆轲》则既不能是传统的英雄人物,也不能说张艺谋式的,所以莫言便设置了一个富有反思精神的角色,不断追问人之为人。据透露,《檀香刑》与《我们的荆轲》的剧场版本也将于年后上演。
2017年的新作剧本《锦衣》是多年以来创作戏曲剧本的圆梦之作。故事的原型是母亲讲的民间故事,深更半夜女儿绣房里面传出男女说话的声音,追问女儿,女儿只好跟母亲交代,每到半夜会有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跟她幽会。她母亲就说,你明天把他的衣服藏起来,女儿听了母亲的话,把小伙子的衣服锁到柜子里,第二天发现鸡窝里走出来一只没有羽毛的公鸡,打开柜子发现一柜鸡毛。莫言在2000年就萌生了创作剧本的想法,但一直到2014年才勉强写好,自觉没什么新意。2017年夏天,莫言发现在清末的时候,一些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受到孙中山的影响,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回来之后变成了反清的革命力量,清政府严令各地严加盘查,就把公鸡变人的故事,跟这段历史结合起来,才有了《锦衣》目前这个剧本的样子。在莫言看来,“即便加上了返清斗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故事依然是陈旧的”,剧本可取之处在于文体的实验和小人物的塑造。因为写唱词要押韵,要运用大量的比喻和联想,满足演员在舞台上大段演唱的需要,真要搬上舞台会做大量的删减;《锦衣》里面小人物变成了主要人物,牙医、媒婆甚至比主角都要多,性格非常鲜明,看出来很小的小人物实际上会影响到历史的进程,县太爷不在的时候,他的爪牙会偷偷跑到太师椅上坐一坐,耀武扬威地体验当官的感受。
莫言认为,一个小说家,应该是一个剧作家,或者一部好的小说的内核就是一部剧,任何一部好小说完全可以从里面改编出一部好的话剧,好的电影或者一部好的舞剧、歌剧出来;而且戏剧对老百姓的影响比小说更大,老百姓这种道德价值观念,就是通过戏曲塑造的。当年陈独秀、梁启超专门论证过,戏曲就是老百姓的教材,舞台就是向劳苦大众开放的教室。

莫言
诺奖后新作:建立在乡村基础上的小说充满开放性
文学读者对“诺奖诅咒”并不陌生,很多作家在摘得这一终身成就奖后,再也没有写出过更伟大的作品。在过去的五年里,莫言周旋于各类公开或不公开的场合,发表着一场场真诚或客套的演讲,在文学的神坛与高密的老屋间,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年轻的时候熬夜写作,现在写的时间比较短,一般是白天写一点,娱乐方式也不多,看看电视,偶尔看看演出,实在不行打开电脑看看冒腔,看看地方戏,有时候翻来覆去听吕剧冒腔的唱段,也是自得其乐。 ”
莫言还在写吗?他会怎么表现当下的中国?诸如此类的疑问也一直缭绕在读者的心头,直到2017年下半年,系列小说《故乡人事》、戏曲文学剧本《锦衣》、组诗《七星曜我》、短篇《天下太平》陆续发表,以及即将发表的《等待摩西》,宣告了莫言从未停止过写作。
2012年春天,莫言在秦岭脚下一个朋友的家里边住着写了一系列作品,后来因得奖便搁置了发表,五年后,这些当年被埋下的萝卜长满了芽子,白菜心钻出了绿苔,要发表就必须要再修改。“这些故事都是有原型的。一位死了的突然活着回来了,一位很落后的突然开上奔驰了,一位很懦弱的突然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总而言之,因为小说里面有人物原型,而且人物原型短短5年都发生了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是能够成长的,而且建立在乡村故乡基础上的小说,本身是充满开放性的,永远不会封闭的。”
陈思和认为,莫言的新作延续了原来创作的基本风格,又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但是根本上还是在写民间深层非常顽强的精神,仍然保持中国民间文化的一种形态,“过去批评莫言的文章也很多,说莫言老写农村比较落后的现象,但恰恰是这些问题表现了中国民间当中很有力量的东西。比如小说里面有一个无赖。这个无赖谁欺负他,这个人像阿Q一样没有力量,被人一打就打倒了。但不管你是村长还是党支部书记还是有钱人,你欺负了他,他不像阿Q只会骂人骗骗自己,他就有自己还击的能力,突然把你家猪毒死了,或者抓住你家的把柄会去告你。中国农民没有话语权,没有能力,弱者会用超出常规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这些都是在莫言以前的作品当中延续下来的,隔了5年一点都不陌生。”
首页推荐
热门推荐
图集
点击排行